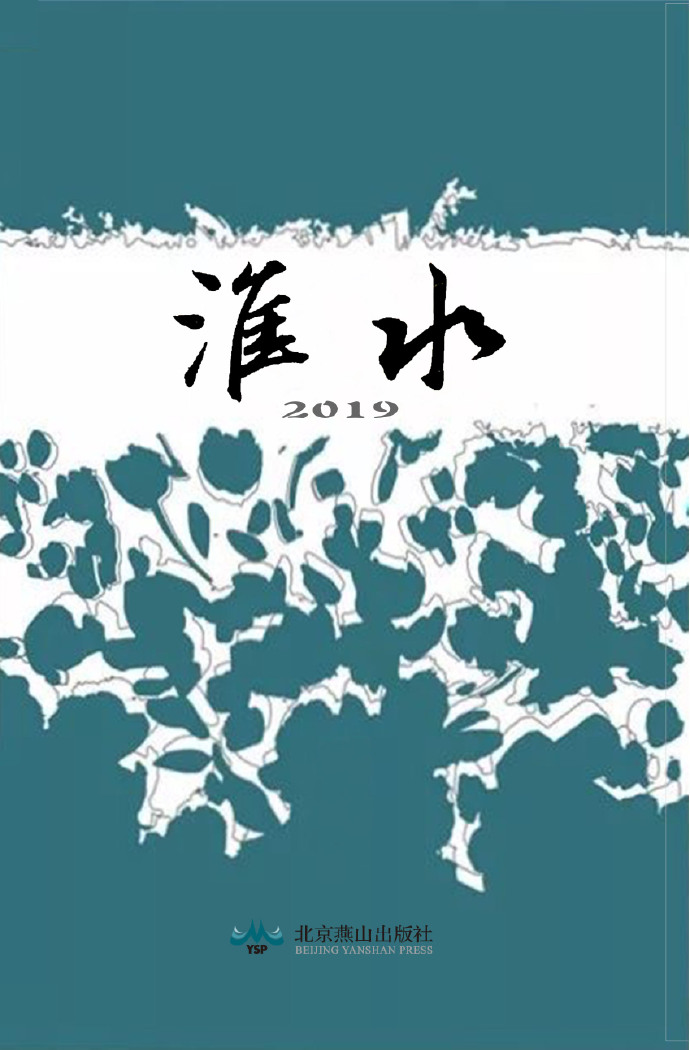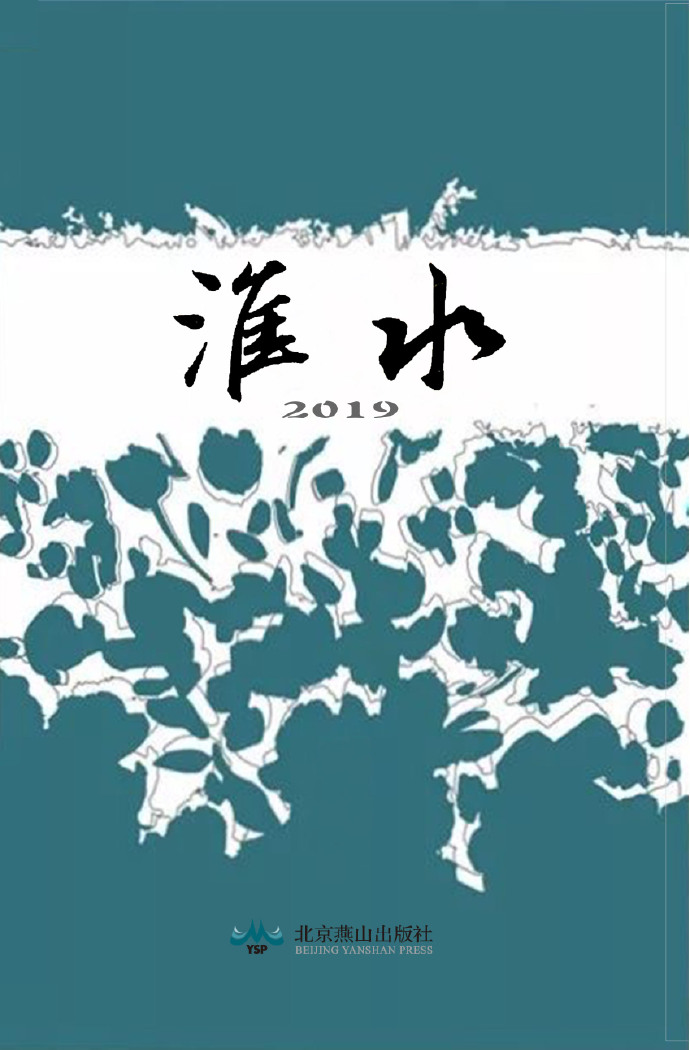
写下这个题目,微信叮一声响了。点开一看,是一个校长朋友转的帖子。抄录如下:
论读书的重要性
不读书,你连捐款留言都写不过人家。
日本捐武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日本捐湖北: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日本富山捐辽宁: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日本舞鹤捐大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中央电视台:武汉不哭
人民日报:武汉加油
这个帖子转得很盛,有心人还做成了大块文字,阅读量很快过了100000+,留言也很盛。不过,我作文的当日,《长江日报》就有文章张目:《相比“风月同天”我更喜欢“武汉加油”》,与那些婉妙的用语对抗。大家还是在文化层面上争,没有骂起来,很好。因为习惯上,夸日本好,就约等于汉奸。
我在这里引用它,不是想借此谈教育,也不是想借此谈文化,这是个超越了教育本身的话题,甚至是超越了许多界限的话题。我把它记录在这里,是想越界说文学。“武汉加油”不是文学,是口号。“风月同天”是偈语,是文学。文学不管什么时候,都自说自话,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文学的个性。当然,作家不是疯子,不能说昏话,不能说过了这一天就成了笑话的话。
一
先要说往流的三个年轻人:丁威、周殿金、王永耀。
三个年轻人都刚到而立之年,他们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都很有成绩,逼着我不得不把关于他们的话题往前提。
过去一年,丁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王永耀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周殿金取得美术学硕士学位,即将攻读美术学博士。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的初中都是在往流镇第一初中读书毕业的。过去的往流作家群成员大多在往流中学浸润过,而他们三位年轻人的突兀而起,标志着往流文化新的创造力量的迅速崛起,快速列队。
在过去十年中,年轻的丁威一直是往流作家群的主力队员。他思维活跃,广泛阅读,善于汲取,不断提升,在散文、小说、诗歌等多个文体创作上都有突出成绩。2019年,是他的年景丰收。继短篇小说获得首届信阳何景明文学奖之后,他的散文集《大河拐大弯》获得第三届信阳何景明文学奖。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这个组织里最年轻梯队的成员,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组织的“中国作家协会2019年度青年会员培训班”。这一年,他通过了河南省文联的招聘考试,即将进入新的岗位开始崭新的生活。丁威的创作突破,不仅对往流作家群、甚至在更大范围内,都是一件令人感到欣喜的事情。相信很多人以不同的心情在期待着。今年《淮水》选入的《我曾见过的粗瓷大碗》是丁威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的节选部分。小说时间跨度较大,人物较多,曲折巧妙地展示了历史巨大变革时期的风云际会和乡村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淮水》多期选择了杨纤如先生的长篇小说《伞》的局部,连续展现一代知识青年在中国历史风云激荡时期的自我选择。作为选编者,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往流作家群新的长篇小说的成型,跨越四十年,与《伞》做个美妙的呼应。
周殿金是往流镇余棚村人,本硕都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他涉猎广泛,专业创作成绩突出,其积极进取的事迹在天津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过,影响了不少年轻学子。不仅如此,他对于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用功很深,成效不凡。他在旧体诗词创作上做过多方面探索,出版了自己的旧体诗集,其中《中华史诗》160行,被多所学校推荐使用,有着很好的反响。他整理、编写、出版了16万字的他的导师、著名花鸟画家霍春阳《霍春阳谈艺录》,成就了一件艺坛佳话。本次选用的他的《浅谈诗书画的关系》是一篇艺谈讲稿,颇有见地,对文艺、文学的创作有启示录的作用。旧话说,烟酒不分家。其实,各种艺术都是一家,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打通其中的关节。关节打通了,三十节的竹竿,其实是一道管儿。高妙一点说,艺术无界限。立此存照,大家各找各的梃杆吧。
王永耀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书法创作上。他是往流镇梁庄村人,1990年出生,毕业于河北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准),作品先后入展中国书法最高奖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首届“蔡文姬奖”全国书画大赛、“贺州杯”全国书法小品展、第五届“中国汝官瓷杯”书画作品大奖赛、第四届中国“海丝”书法大展赛等,目前在深圳从事书法教育。他十多年日日临池不辍,其书法作品正心正笔,工稳雅致,成绩喜人。几年来,往流镇的书法有所发展,往流中学持续举办淮河杯书法比赛,产生较好的影响,本土有五人加入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要介绍王永耀,出于两点思考。一是,一个地方一种文艺形式的勃兴必然带来相关文艺形式的开枝散叶,共同形成地方文化较大的格局。二是往流镇这个地方过去较为盛行的是码头文化和民俗文化,真正排上层面的文化事宜或文化人是很难说出一二的。文学和书法的发展,会很好地推动往流镇朝着文化大镇建设迈步。文化名镇是由文化名事、名人支撑起来的。
二
杨纤如先生无疑更熟悉曾经与他同道的青年知识分子。相比较他的汀泗桥战役和武昌围城等战斗场景的叙述,他写青年知识分子生活和灵魂的笔触更出彩动人。本书选载的《相聚上海》(题目为编者加)写青年知识分子在武汉事件后各自所做出的道路和婚姻的选择与坚守。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由最初的追求单纯的进步,到大浪淘沙后的分道扬镳,各自的未来已初现端倪。杨纤如先生的笔墨沉静圆融,纤毫毕现,丝丝缕缕地探入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细微处,去描绘,去开掘,去展示。
文学创作自有自己的难处和高处,与其他艺术样式相比,它拒绝重复,也无法复制。一个书法家一生可以轻而易举写上100幅“清明时节雨纷纷”,一个花鸟画家一生至少画上50幅花鸟虫鱼,剪纸剪出多少老鼠娶亲呀!但是,作家无法这样做。作家重复写作叫“打滑”,既指题材的打滑,也指水平的打滑。作家写作要始终处于处心积虑状态,总要在开疆拓土,总要在弃旧图新,总是在挥手告别。这是铁律。如果一味驾轻就熟走下去,最多在量上有所积累。
赵主明先生年届七旬,却始终笔耕不辍,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停下向前的脚步,总有新思考,新发现,新表达,《飞起求生》是个新成果,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短美文年选。蒲公英是寻常物,因为它自备有伞,借风传播,生命“自度”,自我飞起求生。蒲公英这个诗意的另类,被作家赋予了深层次的人生思考。相较许多生命,或果熟蒂落,或等待啄食,或坐在脚下瘠薄的土里,或安逸地享用,或牢骚地抱怨,或坐等启用,有多少飞起求生过呢?《飞起求生》这篇精短美文,带给人许多思考,不妨把它当作一篇成长经文教给孩子。
赵主明先生的散文善于撷取日常生活中极细微的点滴,叙述升华,映射光芒。《回老家的路》初看去,不过是一篇产生于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之际的应景之作,但稍一细读,会感到行文中浸润的温情与至醇。
有年夏天,岳父病逝。处理罢公务,连夜赶回。到达镇上,朋友准备了一把雨伞,一个手电筒,我谢绝了他们护送,拐上乡间小路。雨下小了,干脆收了伞,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握着手电筒。四野漆黑一片,脚下迸着泥泞,耳畔虫声唧唧,偶尔几声蛙鸣,稻田里响着哗哗的水声。我关掉手电,停下脚步,站了一回,感受一下乡间的雨夜,几分恐惧,几分悲伤,几许无奈,一齐涌上心头。不敢多停,继续赶路。到家时,妻子一惊,埋怨说:“怕你夜里回来,咋不等明天一早呢。”
读到此处,心头会突然受到撞击。这是来自细节的力量,来自深刻体味的力量。粗线条的叙述文本,是无法产生这种令人心灵悸动的效果的。
赵主明先生近年创作以随笔为主。我是把随笔一律称之为散文的。如果硬要细分赵主明先生的散文为随笔,那么,我认为他的随笔特点表现为“随性”:有所触动,性之所至,信手拈来,连缀成文,写目之常见,世之常态,心之常情,不翻案,不惊悚,不故作姿态,不卖弄学问,满是暖意,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然而,毋庸置疑,他的作品是用心的,那是一生佛号一生心。他的作品是动情的,那是幽篁明月无限情。有佛的大化,有道的悠然,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佳境。
大学者王国维曾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我们的很多作者,不愿、不敢、不能呈现自我真实的经验,往往提笔之初,就产生了完成命题作文的心态,用既定的、流行的并且往往是陈腐的认识去过滤自己复杂而真切的体验,得出的是四平八稳的文字。这样的文章不是没有认识,而是在重复他人的认识,写作也因此是“重复他人说过的话”,不仅没有“高致”,而且连本来的“生气”也丢掉了,是很可惜的。其实,我们自身的经验中就不乏“生气”,静心想想也会有对存在之“高致”的切近。胡亚才的《一次失聪》写的是自己突然遭逢失聪的事,面对繁重工作中的变化、亲友情感生活中的波澜,作者内心百感交集,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一个生命的承受之重和抉择之难。一番波折之后回复到生活的正常状态,作者选择了不失原则立场的砥砺自我的方式——大步走,也获得了饱含痛感的生存反思:“我失聪那刻的惊慌失措与随之而来的所谓的镇定,除了本能的反应之外,与其说是对曾给我带来诸多益处的这一技能类的功夫难割难舍,倒不如说是我对曾经拥有过的名声与胜负中的成功喜悦的迷恋。”这番反思可谓是对宋儒陆九渊那段话的自我诠释,也是作者对生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而获得的人生“高致”。(吕东亮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亚才先生在繁杂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余,还能拨冗静下心来沉思、深思、哲思,并付诸于笔下的文字,真的不敢想象他是如何调配时间的。
三
生活对于每个人的赐予都是一样多,我们每个人留住的多少却相差较大。正如以手捧水,指缝宽的都漏干了,指缝紧的就掬起了。生活之于写作者也是如此。今年入选的任龙业和杨培建两位作者就紧紧抓住了生活的馈赠,写出了令人动情的文章。他们的散文突出的特点就是扎实,真实,带着人生的原色,原味。
任龙业对于往流作家群来说,是一位迟到的战士。他生活经历丰富,而每一个阶段的赤橙黄绿都被他细心地打包收藏,发酵成创作的材料。他在海南岛当兵的蓝色披肩,援藏工作的异域风情,大学读书的难忘时光,都一一深情地纳入笔底,洋洋洒洒,蔚为壮观。写这样的文章对散文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种生活容易写成流水账似的回忆录,籽粒干瘪,味同嚼蜡。但他的答卷是出色的,他的散文不仅展示自己特定时期的流金岁月,更是很好地融入了不同时期的历史风云,显得厚实丰盈。他的散文深情款款,气韵丰沛,场面开阔,细节真切,融洽契合,不留痕迹。他善于把握特定历史时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互关系,将自己的生活穿插进特定的环境里去勾画描摹,穿插跳宕。这次选编他的《我的大学,我的梦》是一篇长散文,一万四千多字,完整地叙述了特定时期自己的大学生活,既光怪陆离,又斑斓多彩。他嘱咐我由于篇幅原因最好分两年用,在我一气呵成不能遏制自己地读完之后,我就决定违背作者的意愿,奢侈地一次用完它,不让大家读着读着还难受地吊一年的胃口。好文共赏,先睹为快。任龙业的创作给往流作家群创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的标杆,值得去比比靠靠。
杨培建在往流中学读过书,执过教,做过省报记者、编辑,市政府职员、官员,对生活和社会的各个场都沉得深,摸得透。所以,他的作品也深刻地浸透了多种杂色和难言的味道。他早年的散文有较多的社会反思和激进的历史批判,思想敏锐,长于思辨。多年来的身世沉浮,也让他在屈伸之间多了些技法和吞吐的方式。这个资深写作者今年首次亮相《淮水》,成为往流作家群的一员,带来了散文《老家旧事实录》。这篇散文采用口述实录的方式写作,每篇都有讲述人、讲述地点、讲述时间,形式上给人不少新鲜感。它共有三个特殊时期令人瞠目的故事组成,织就了一幅特殊时期的乡民生活图景,读之令人神伤。漫过我们身边的云淡风轻的日子很多很多,欣赏风花雪月容易成为常态,然而,艺术的极致价值常常在于记录某些风狂雨骤的摧折,以警醒人们好日子中容易出现黑斑、霉斑。期待着杨培建能不断拿出新作品,增色《淮水》。
四
今年《淮水》稿件相对较为丰富,也是很少见的在选稿中忍痛割爱。梳理本年度稿件,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型。
1.怀旧类。
怀旧散文仍占有相当的数量。虽人生匆忙,世事沧桑,乍回首,昨日仍带余温,行之不远,倍加难忘。总结也好,留恋也好,反思也好,信手拈来,最易成章。今年的怀旧散文同往年一样,佳作迭出。除了上文提到的任龙业的散文、杨培建的散文,《回老家的路》等,还有不少值得咂摸的作品。
赵承先老师今年再出新作。提到他,我们充满敬意的是除了他作品本身,还有他耄耋之年的不懈坚持。他的这篇散文写母亲的艰辛时光,令人动容。他的孝心回报让他成了小镇的样本。
张弘散文《春风沉醉的晚上》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小桥流水,淙淙潺潺,花开江南,燕飞雨斜。青春的萌动和煦暖,恰适合这种语言氛围。虽旧事重提,不免心生怅惘,却声色不减。
魏建东是典型的慢工出细活,他的散文《黑鱼》《马蜂》精致细腻,神秘有趣。他选取童年的视角对动物进行观察描摹,展示生动有趣的一面,保留神秘莫测的一面,很用心思。写作需要故弄玄虚,需要装聋作哑,需要装痴卖傻,需要故弄关节……这些都是技巧。这些技巧在他的散文里都有很好的使用,才将乡村旧事写得童趣盎然。
王传银今年也以“新秀”登场,第一次从他若干压箱底的稿件中拿出一件来。王传银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多年写作不辍,车里总是放一本年度的《小说选刊》给我印象最深。他年年关注着《淮水》,关注着往流作家群的创作,每每有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今年他难得拿出了一篇《你做过小偷吗》,于旧事琐屑中足见历史的影像。
老作者中,周明金的散文《月当头》《旧时年味》都在民俗的书写中怀念旧日慢慢消散的节日仪式感。多年里,他拿出很多精力和时间,致力于往流镇一带民俗文化的挖掘、搜集、整理,颇有成效,为后人更多了解往流的民俗积累了财富。
李成猛是一名勤奋的作者,几年里,创作数量可观。他精心于对乡村品物的精雕细刻,自成一格。2019年,他的散文《葫芦瓢》被学习强国推荐为学习材料,《依依南瓜情》被《中学生阅读》选载。
郑孝青的散文《牛铃声声远》写农人与畜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乡村少年的牧歌生活。时玉和的散文《田野上的滋味》感谢大地田野的馈赠。熊志贺的散文《白露河畔放牛求学记》的旧日片段书写中有洒脱的跳荡,这与他具有生活的俯瞰能力有很大关系。
这些怀旧作品都是他们生活的浓重的影子,此刻记录下来正当其时,下一代人看来就只能滋生怀古的情绪了。惜多行文仓促,细节上缺少驻留的眼神,不免给人匆忙之憾。
2.游记类。
大致每年都有一些游记之作。到天涯海角如同昔日走趟亲戚赶个集,脚步所到之处多了,便想记下所观所感,以佐证不虚此行。文人容易纵情自然,古往今来,好的游记文章、游记著述很多,灿烂着中国文学宝库。
王散木老师的《乌拉盖,人文浸润的天边草原》一如他的此类游记散文,取景独特,开阔大气,让人感到如同广角长镜头在多面摇曳地观览风景。关于狼性,关于知青,给这片天边的草原注入了全新的元素,甚至灵魂。草原都是好地方,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油彩的绘画美,而超越这种美的是草丛里惊心的眼光闪动。
胡烈刚的散文《昆仑山寻宝之旅》是一篇奇特的游记散文,延续了他擅长的歌诗一体的写法,歌之咏之舞之蹈之,腾挪跳跃,节奏感很强。他把国家与玉、文人与玉、采玉之险与昆仑山的奇幻糅合起来,交织出了玉文化之经、采玉旅程之纬的篇章。
周殿传的湘西游记还在继续,继去年喝茶之后,今年在唱歌。湘西的歌多,比刘三姐还多。湘西每一种仪式上都要唱起来,无论是悲还是喜。周殿传的游记有更多振铎采风的意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湘西歌吟文化的材料。
3.现实类。
现实生活之于作者来说,是热烫烫的,无法回避,不容回避。作者可以像勇士一样,不瞻前,不顾后,但他必须和自己的影子一起,站在阳光下,打量自己。
陈学新的“非常打工生活”保持着他一贯的语言麻辣烫味道,把开放前沿各色人等、各样生活活剧合盘端出。他的语言俏皮乖张,摇曳多姿,能将一桶沉重的浊水瞬间氤氲开去。语言的个性化在陈学新的作品中特别鲜明,因而,他的作品就容易让人多看一眼。
刘学鹏的散文《往来于桥头》是他在工作新岗位上的新作。他迅速地把桥头的特色线条凸凹有致地勾勒出来,字里行间,心潮暗涌。更可贵的是他嵌入了香港2019的烟色,让《淮水》的呼吸开阔且前沿。
张玉萍是今年唯一入选的女作者。她的散文《插秧的记忆》《帆的赞歌》都是写亲情的,所选取的事物、片段、瞬间,都令人难忘。这两篇散文匀称、厚重、扎实,把事务中的人,人肩上的感情,都表现得丰赡而饱满。她对生活的掌握很稳,没有丝毫的漂浮与矫情,起笔落笔,感情真挚,不虚饰,不伪情,弥足珍贵。
4.言论类。
中国最早的散文源头之一就是言论,诸子百家把言论散文推上了高峰,历代延续,成为传播思想、哲学的载体。《淮水》多次发过言论散文,有胡烈刚的“哲学与艺术”,周殿金的论教育……今年的言论类稿件算是较多的,质量也很好。
杨新华到南方工作20多年了,他时时关注家乡的人和事,今年第一次把这种关心放到了《淮水》这个平台上。他当过教师,当过校长,而后多年在行政岗位上摔打,但初心依旧。他的《似曾相识燕归来》把对家乡的情愫融入到对家乡的发展的人才渴盼之中,且建议,且呐喊,热切,急切。
余大胜多年钟情于文学,对传统文化,旧体诗词,都很倾心。他虽然大学毕业后一直从商,但对文学艺术的情致始终不减,时有诗文出世。他的《孔子有多么喜爱<诗经>》可看作是一篇文化普及类文章。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淮水》里说过,我们真的要读一些文论、论文、评论,否则,写作容易缺底气。余大胜的做法和文章,特别是周殿金的艺术论,都可以帮助我们阅读发端。
窗外的雪纷纷扬扬,这是庚子年的第一场雪,很像样。闭门观雪,网上和朋友除了谈些旧日的雪中故事,互相反复叮嘱的还是难以琢磨的疫情。文学是无力的,想借助它去抗疫,几乎等于去借灯草打狗。如果说文学机构里养着人是为了他们吃饭,可到底我们弄文学干什么呢?
熊西平
2020年2月15日竣工 雪